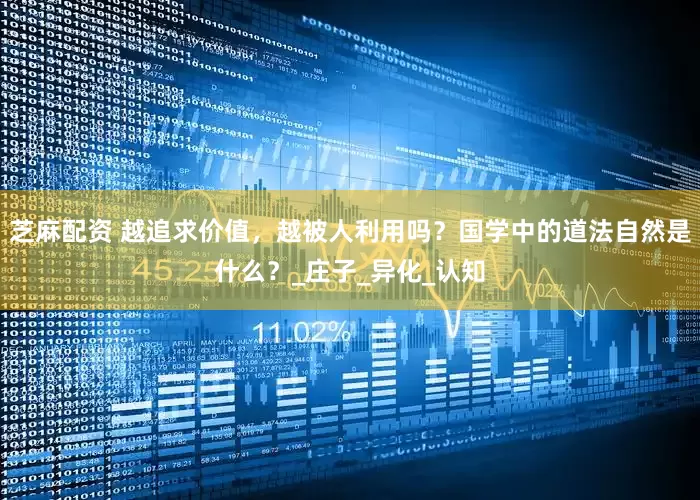
《庄子・山木》记载了这样一个寓言:山木因 "可用" 而被砍伐,膏火因 "可燃" 而被焚烧。后世文人常以此感叹 "有才之患",却很少追问:当我们以 "价值" 为标尺丈量万物时,是否早已陷入人为建构的认知牢笼?甲骨文中的 "值" 字,本像人持戈守卫酒坛,原初含义是 "守护本真",而现代语境中的 "价值追求",却异化为对功利符号的追逐 —— 这正是老子所谓 "天下皆知美之为美,斯恶已" 的当代注解。
儒家强调 "君子喻于义",但《韩非子・五蠹》早已洞察:当仁义成为显学,必有 "仲尼为政而鲁乱" 的悖论。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,各派学者争鸣 "帝王之术",最终却沦为诸侯争霸的工具,恰似《庄子》讽刺的 "儒以《诗》《礼》发冢"—— 当价值追求脱离了内在德性,必然异化为被他人收割的 "概念韭菜"。
展开剩余78%二、道法自然的真义:解构 "人为" 的认知屏障"道法自然" 出自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,河上公注曰 "道性自然,无所法也",王弼释为 "法自然者,在方而法方,在圆而法圆"。这里的 "自然" 并非物理自然,而是事物本然的存在状态。甲骨文 "自" 像鼻子,引申为 "自身本真";"然" 通 "燃",象征本然的生发状态。所谓道法自然,本质是破除 "人为" 的强行干预,让万物各遂其性。
《周易・系辞》言 "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",这种 "观物取象" 的认知方式,与道家 "心斋"" 坐忘 "异曲同工。宋代邵雍《观物篇》提出" 以物观物 ",反对" 以我观物 ",正是对" 道法自然 " 的认知论展开 —— 当我们放下功利心去体认世界,才能看见事物未被价值标签污染的本真面貌。
三、价值异化的破局:从 "有用" 到 "无用之用"庄子与弟子辩论 "无用之树" 时说:"今子有大树,患其无用,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,广莫之野?" 这里的 "无用",并非消极避世,而是超越工具理性的价值重构。明代王阳明在龙场驿悟得 "心外无物",正是意识到:当我们以功利心赋予事物 "价值",实则是用意识牢笼囚禁了世界的无限可能。
《道德经》第四十八章 "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",揭示了两种认知路径:"为学" 是不断叠加价值判断,"为道" 是逐层剥离人为建构。就像青铜器上的饕餮纹,初为祭祀重器时承载威严,当剥离符号意义,不过是铜锡合金的自然氧化 —— 真正的 "价值",藏在破除执念后的本然显现中。
四、现代性困境的国学解方:在有为与无为间守中
晚清思想家郭嵩焘曾说:"西洋立国有本有末,其本在朝廷政教,其末在商贾器械。" 这与《周易・乾卦》"刚健中正" 的智慧相通:真正的价值追求,应如 "天行健" 般刚健不息,同时保持 "用九,见群龙无首" 的自然状态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以 "作为人,何谓正确" 为决策基准,正是将 "道法自然" 转化为现代商业伦理。
面对 "越追求价值越被利用" 的困局,《孙子兵法》"致人而不致于人" 提供了破局之道:当我们以 "自然" 为价值锚点,而非外界定义的功利标准,就能在 "有所为有所不为" 中保持主动。就像古琴的泛音列暗合斐波那契数列,真正的价值,从来存在于与自然节律的共振之中。
在价值荒漠中守护本真之泉敦煌写卷《老子想尔注》有云:"自然者,与道同号异体,令更相法,皆共法道。" 当我们被消费主义的浪潮裹挟,将 "成功"" 财富 ""地位" 异化为终极价值时,不妨回到甲骨文的原初智慧 ——"价" 字从 "人" 从 "介",本指人与人之间的界限;"值" 字从 "人" 从 "直",象征保持本真的直立人格。
国学中的 "道法自然",从来不是消极的避世哲学,而是教人在价值迷宫中持守 "直方大"(《周易・坤卦》)的生存智慧。就像故宫太和殿的 "建极绥猷" 匾额,既需 "建极" 的价值建构,更要 "绥猷" 的自然顺应。当我们学会以 "无用之用" 的眼光观照世界,那些曾被工具理性切割的价值枷锁,终将在 "道法自然" 的光照下,显露出万物一体的本真面容。
在这个价值通胀的时代,或许我们最需要的,不是更多的价值追求,而是像庄子那样,在濮水之畔对楚王使者说:"吾将曳尾于涂中"—— 在保持本真的 "自然" 状态里,让生命的价值,如春风化雨般自然呈现。
发布于:上海市日升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